史铁生逝世10周年:在轮椅上度过了38年的他,为什么被称作“时代的巨人”?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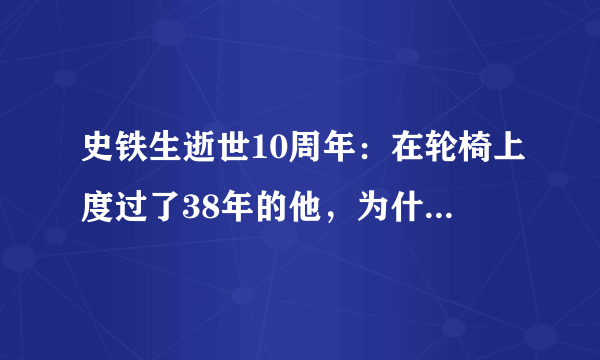
个体的消亡,于浩瀚的时空而言,渺小得无足轻重,但对于具体的生命来说,则意味着永恒的寂灭。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像一场来不及告别的意外,哪怕他生前曾说,“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恍然间,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10年。
10年里的翻覆可以称作“沧桑”,但在那些未曾忘记的频频回望里,他的身影与文字似乎还清晰如昨。
史铁生出生那天,北京天降大雪。
“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蹚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屋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
俗话讲,瑞雪兆丰年,但那天的大雪,却拉开了他苦厄人生的一个预言性的悲怆序幕。
“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
▲ 史铁生和母亲
但母亲没想到的是,那个出生伊始并没有被她惜若珍宝的儿子,后来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史铁生十岁时就在作文比赛中拿到第一名,中学在清华附中就读,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如果不是十年浩劫,他一定会成为天之骄子,前程远大。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18岁的史铁生报名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
他自幼患有先天性脊椎裂的毛病,母亲的忧心忡忡并未遏止住他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实施。
但一腔热血,再豪情万丈,也难敌现实的残酷。
饥饿是首当其冲的考验。
他常常是干了一天的活,晚饭却只是一碗稀粥。很多时候饿得辗转反侧,他就效仿老乡,抓一小撮盐,兑上一碗水,大口灌下。
趁着饱胀感,赶紧睡觉。
睡在几乎呵气成冰的窑洞里,他的脊髓长期遭受寒凉的侵蚀。
后来因为腰病加剧,他被派去喂牛。他从不偷懒,数九寒天的半夜,也要起来好几趟给牛添草加料。朔风砭骨,为他的身体悄然埋下了祸根。
▲ 知青时代的史铁生
得病前的史铁生,是孔武有力的小伙子,健壮得可以抱起一头小牛,但每况愈下的病情却让他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71年9月,行走都已经困难的史铁生,不得不离开陕北,回京治疗。
因为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且病情严重,一年后,他的下肢彻底瘫痪。
入院时,他被父亲搀扶着走进;出院时,他则是被人抬着回家。
那年,他只有21岁,却从曾经健步如飞的跨栏冠军变成了一个被轮椅牢牢束缚住翅膀的人。
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的青春戛然而止,提前进入人生的暮秋。
双腿瘫痪后的史铁生,变得异常暴躁,一心求死。从发病到截瘫,他自杀三次,皆未果。
母亲对他寸步不离,悉心照料。
▲ 史铁生和地坛
那时,她千方百计地淘来各种偏方,让他吃,让他喝,或者是洗、敷、熏、灸。
但都无济于事。
史铁生坐上轮椅后的整整七年,是他生命中最绝望的至暗时刻。那些年,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比残疾更令他痛苦的是,他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弃儿”。
那时,他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和前途、平等和尊严,还有爱与被爱的权利。
▲ 1980年代中期,史铁生在雍和宫的家
曾经有一个女孩闯进他的生活,让他在千里冰封的世界第一次感受到万丈阳光的照耀。但因为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女孩不久就消失了。
他再一次被抛掷在无边的荒原上和巨大的虚空里。
就像他后来在《命若琴弦》里写的小瞎子,在心爱的女孩嫁到山外时,小瞎子一个人跑到了深山里,当老瞎子找到他后,他哭了几天几夜,问老瞎子:“干嘛咱们是瞎子!”
被命运“钦点”的困境,很多时候我们都无力改变。最终,是地坛收留了魂无所依的史铁生。
作为古代帝王祭祀的场所,曾经鼎盛昌荣的地坛,在剥蚀了朱红,坍圮了雕栏后,成为他孤独心灵的栖息地。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后来,他经常带着笔和本子,躲在安静的、不被人打扰的角落,潜心写作,与天地万物对话,与人间苦难对话,那是他在茫茫大海上抓到的唯一浮木,是他对自己最后的救赎。
有好几次,他在园子中呆的时间太久了,母亲不放心,便来寻他,但只要看到儿子还好好的,便悄悄转身离去。
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儿子脆弱的自尊,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煎熬与牵挂中惦记着他的安危。
那时,她一遍遍地去跑劳动局,想给儿子申请一个铁饭碗。
素来自尊要强的母亲低声下气,向每位来往的人员推销儿子:
“孩子坐在轮椅上,也可以胜任很多工作的。”
那天,他们见到的最后一个人,直接对母亲说:
“回去再等等吧,全须全尾的我们这儿还分配不过来呢。”
那时的母亲已经重病在身,但她一直瞒着史铁生,执意为儿子去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差使,她显然是在安排身后事:她一定是希望在自己走后,儿子还能靠双手养活自己。
1974年,史铁生终于到北新桥街道生产组当临时工。
他每天摇着轮椅到工厂去上班——在仿古家具上画画,每月挣十几元钱以补贴家用。
不久,母亲因肝病去世。
“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邻居把母亲抬上车时,她正大口大口吐着鲜血。
母亲走的时候,只有49岁。
“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的去世,将史铁生推向了一个更加深不可测的渊薮。有母亲在,他还是一个可以任性的孩子;母亲不在了,他失去了生命中最大的靠山。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他开始在对母亲的愧疚中反省自己面对厄运时的懦弱与自私。
“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四年后,史铁生才敢慢慢回忆母亲的生前事,在无尽的追思中,落笔写下《秋天的怀念》: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30岁那年,史铁生因泌尿系统感染、氮质血症、肾盂积水,多病齐发,进行膀胱造瘘术。
那时的他被医生预测只有5年的寿命了。
一年后,史铁生又因为急性肾损伤而不得不辞去了街道的临时工作,回家休养。
在生命“倒计时”的过程中,他将与疾病搏斗剩下来的力气全部用在了写作上。
他在《务虚笔记》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所有的写作之夜,雨雪风霜,我都在想:写作何用?
写作,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肩上和心里感到它们的重量,甚至压迫,甚至刺痛。现在才能存在。现在才能往来于过去和未来,成为梦想。”
在《命若琴弦》中,老瞎子告诉小瞎子,要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得到治病的药方。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诓骗小瞎子好好活下去的弥天大谎。
纵然寄蜉蝣于天地,但如果没有希望高悬,人怎么才能活下去呢。
1983年,史铁生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当年《青年文学》的编辑牛志强一遍读毕,“就沉浸于莫大的感动和喜悦之中!连夜进行编辑加工,写推荐意见,竟不知东方既白......”
此后,他的创作一发不可收。
当年,史铁生住的小屋只有六七平米,屋里除了床和写字台,余下的空间仅够轮椅转个弯。
那时,经常有慕名而来的朋友去看他,他们感叹于在那方逼仄的空间里,他能创作出那些装得下浩渺的忧患与哲思,以及世间一切终极之问的作品,他们发现,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全然没有他们想象的颓唐和愁苦。
相反,他喜欢聊好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他对一切有趣的事物深深着迷。
逸兴遄飞,天南地北,无所不涉。
作家王安忆第一次去看他,以为史铁生会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会慨叹命运无常。结果史铁生自始至终都在和他聊美食。
王安忆不由感叹:史铁生的乐观和率真,让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都自愧不如。
即使是看似顾影自怜的《病隙碎笔》,读起来也毫不怨天尤人,始终洋溢着通透与达观: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
没有人生而坚强,他只是不想成为战场上的“逃兵”,于是,“扶轮问路”,于荆棘丛生中摸索前行。
疾病发展到后期时,他身体衰弱得连待客都无多余精力了,但只要有朋友到访,他又强打精神,与之谈笑风生。
人如果不能超越自己的遭遇与痛苦,就只能被痛苦所吞噬。他不想溺毙于无边的海洋中,于是,哪怕在最饱受疾病摧残的阶段,他仍利用一切清醒的时间去创作。
向死而生,让他笔下的文字充满了对意义之辩的叩问,对人类信仰的探求:
“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
史铁生一生总共写下了28部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2部长篇小说,15部随笔。
他自嘲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时间写点东西。”
于他而言,文学创作是让他在尘世获得超越苦难力量的一双翅膀,他驾驭着这双沉重而又轻盈的羽翼,飞跃高山与大海,俯瞰芸芸众生,与世间的一切悲欢与生死。
在中国古老的辩证法中,祸福相倚,得失互生。似乎吃了太多苦的人,也会偶尔尝到命运赐予的一点甜。
史铁生最初进行创作时,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爱情的命运》,文笔沉郁,吸引了一名女编辑的注意。
这名女编辑叫陈希米,当时任职于西北大学所办的刊物《希望》。
▲ 史铁生与陈希米
因为欣赏史铁生的才情,陈希米开始与他通信。
他在北京,她在西北,关山迢遥,两人的书信往来长达10年,却素未谋面。
两人初次见面却已是1989年的春天。
因为那一年,史铁生再次住进了医院。
千里之外的陈希米,匆匆赶到他的病榻前,就像当年他的母亲那样,对他用心照拂。
当年,陈希米28岁,左腿有轻微残疾;史铁生38岁,双腿无法行走,诸病缠身。
▲电脑PS,让他们青梅竹马。(史铁生、陈希米制作)
但相同的灵魂,总会跨越千山万水,于千万人之中相遇。
他一向拙于爱的言辞,她却让他破天荒地诗意泉涌:
“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樊篱。”
▲ 史铁生与陈希米
对于他们的相爱,有人调侃为“瘫子配瘸子”。
然而他们超越世俗眼光的爱情却远胜于很多健全之人的结合。
1989年,史铁生与陈希米结婚。
一鼎一镬,一饭一蔬,他们将寻常的日子过得云蒸霞蔚。
当史铁生身体稍微康复一些的时候,陈希米就推着史铁生去看电影,去大街小巷找史铁生爱吃的小馆子。
照顾史铁生这样的病号,对于娇小瘦弱的陈希米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但她坚持亲力亲为,不请保姆。
闲暇时,他们一起读书,一起谈天说地,他给她讲自己的过去,讲他的母亲,讲他的初恋,给她念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
多少人爱过你昙花一现的身影,
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真情,
惟独一人曾爱你那朝圣者的心,
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
她总是听得热泪盈眶。
史铁生病重卧床,无法写作的日子里,陈希米就成了他的笔。他讲述,她记录。
她说:“我是铁生的妻子,所以才要做更好的陈希米。”
好友陈村曾感慨乐观明媚的陈希米给史铁生带去的阳光:
“我永不能忘记的是她的笑,那是天使的笑容。天使的笑,是那种忘忧的笑、忘我的笑、来去自由的笑、让看见的人也喜悦的笑……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
作家铁凝回忆她去史铁生家里作客的情景,虽然夫妻俩都行动不便,但小日子过得烟火俱足,有滋有味:
“一个不足70平米的小房子里,陈希米亲自和面团、烤面包,这个充满面包香的家,整洁、朴素、温暖,那样的有尊严,他们过的每一天,都那么有情有义。”
在史铁生病危之时,陈希米就在病床边陪伴,只要她一离开,他的心电图就乱了;她回来,他便好了。
▲ 史铁生与家人
他曾在书中写道:
“她是顺水漂来的孩子,但不是我捞起了是她,是她捞起了我。”
爱神将他打捞上岸,死神却如影随形。
1998年,史铁生的肾病越发严重,最后恶化为尿毒症,再度住进了医院。
本来是男人最意气风发和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却不得不频繁地进行血液透析,依靠导尿管来生活。
他的透析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两次。
再后来,两天一次。
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以透析维持生命的人常规化的治疗手段,但于他而言,是一次次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往返的中转站。
每次透析,他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看殷红的血在体外汩汩地循环过滤,再循环,再过滤,然后重新回到自己耗竭殆尽的身体里。
身体里的血要过滤十几遍。每次透析长达4个半小时。
这样的日常,持续了整整12年。他的手背上,血管隆起,状如蚯蚓,那是针刺过1000多次的后果。
他先后住过三家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朝阳区医院、宣武区医院。住过时间最久的医院是友谊医院,12间病室,他住过10间。
因为住的时间最长,透析的次数最多,他成了医院的“透析模范”,和他早已熟䄒的护士说他:“你的名字真的没取错,你的命比铁都硬。”
他的主治大夫见惯了生老病死,人间疾苦,却经常感叹史铁生面对病魔的从容与豁达:“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
他曾说,“就算这心灵之墙可以轻易拆除,但山和水都是墙,天和地都是墙,时间和空间都是墙,命运是无穷的限制,上帝的秘密是不尽的墙。”
所以, 面对上帝制造的无穷无尽的铜墙铁壁,或者破墙而出,或者直接面对。我们往往赞美无往不利的胜者,但实际上,能泰然直面的人,已经是勇士。
在《我与地坛》中,他写道: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突发脑溢血离世,享年59岁。
距离他60岁生日,仅差5天。
他被推进太平间时,陈希米流泪叮嘱朋友:“给他多盖点儿,他怕冷......”
按照他生前的意愿,他身体所有能用的器官都实现了捐献,他曾说:
“希望器官新的主人能帮我继续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即使是他认为功能比较弱的肝脏,也成功移植给了一个天津肝病患者。
作家韩少功如此评价他:“史铁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
他对妻子说过,“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
史铁生离世后,陈希米在巨大的悲恸中写下了《让“死”活下去》。
“在我的生命里,只要还以你为坐标,只要还以史铁生作为我的你,史铁生就还在,饱满地在。”
她早已想好了自己的墓志铭:
“下一世,我还将顺水飘来。”
如果有来世,他们能再度重逢,他也许仍愿自己是被她在命运的岸边打捞上来的孩子。
他在一篇文章里预见性地谈过自己的“归宿”:
“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无极,生生不息,绵亘于岁月的长河,除了人类的尊严与勇气,也许,唯有爱与希望才是最好的延续。
毕竟,那是一个时代最为丰赡的存在。 文/荠麦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