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生态观:如何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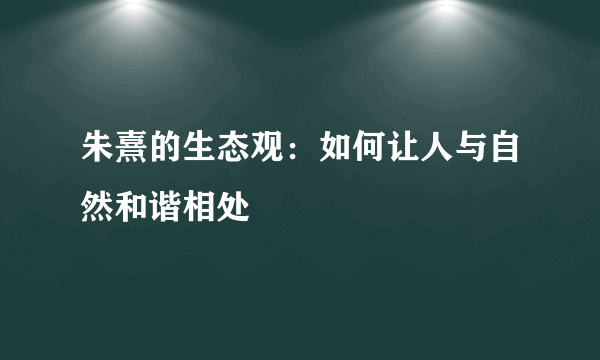
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埋下了不可预料的隐患,引起人们的焦虑和不安。人们不得不多方反思,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溯古人的生存智慧。朱熹作为儒家的集大成者,其关于人和物的思考建立在人与万物同宗同源的基础之上,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为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认为人与物是统一的,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对《中庸》进行注解:“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认为天在创化万物的过程中,一方面以“阴阳五行之气”聚合成万物之形,另一方面,将“理”赋予万物,这样一来,万物与人一样都具有天赋予的共同之“理”,由于他相信“性即理也”,由此,万物又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既然人之性与物之性都来源于天,所以人与万物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本性。这种观点在《朱子语类》中也有相关的表述:“‘性’字通人、通物而言。但人、物气禀有异,不可道物无此理……仁义礼智,物岂不有,但偏耳。”在这里,朱熹明确表述自然万物与人一样,也有仁义礼智之性。朱熹认为不仅是动物有着与人共同的“性”,而且花草等植物,甚至是无生命的物体也具有。“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花瓶便有花瓶的道理,书灯便有书灯的道理。”
《朱子语类》
如果说人与物一样有着共同的“理”与“性”,是不是可以说人与物是完全无差等呢?显然不是的。朱熹所说的人与物的统一,是从人之性与物之性两者来自同一个本源而言,认为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具有差异。但人与物仍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就在于人与物的“气”有差异。朱熹在《孟子集注·告子上》注孟子所说的人之性与牛、犬等动物之性时,说:“人、物之声,莫不是有性,亦莫不是有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在朱熹看来,人与物的气禀是不同的,导致人的仁义礼智之性是完善而整全的,而物的仁义礼智之性是不全的,因此,人是万物之灵。
人与物统一于“理”而异于“气”,作为行动的主体,人要承担起道德责任与义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并在完善自我的基础上推己及人、由仁及物,通过与自然的互动,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由此,朱熹提出了自己关于人应当如何对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是怎样的。《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的作者乐爱国认为,朱熹提出人与物由于气禀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圣人应当对人与物的不同品级而做出节制和约束,立礼、乐、刑、政之属,以教化天下,而这种教化不只是在伦理道德方面,而且也包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物方面,而使“万物各得其所”。
《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乐爱国/著,海天出版社 2014年3月版
朱熹在人如何对待自然万物方面对人的作用定位是“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是人要参与到自然当中,人与自然进行互动,并辅助自然,这一句集中了朱熹对于人类在参与自然过程中各种行为的高度概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他认可程颐关于“赞”的解释,《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中程颐提到赞化处,说:“天人所为,各自有份”,这种说法得到朱熹的赞同,而且,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他给“赞”下了定义,“赞,犹助也。”在朱熹看来,天和人各自有各自的分内之事,天有天所要做的事,人有人所要做的事,而人所要做的就是“赞天地之化育”,“赞”取“赞助”之意;另一方面,朱熹进一步将“赞”引申为根据天地之道,教化百姓依道而行,即“裁成辅相”,这一词来源于《周易》。由于世间万物都有其不足之处,而只是生成了人和万物,赋予“道”和“理”,而天自己是无法使得万物依道而行,无法做这些事情,因此,需要圣人来教化百姓与万物。总的来说,就是根据天地之道,来“赞助”和“辅佐”天地所不能做的事,使万物得以完善,依道而行。
“赞助”与“辅佐”是朱熹对人参与自然的作用的总括,那么人应当如何发挥这种作用呢?朱熹认为,只有“尽物之性”才能达到“赞天地之化育”。所谓“尽物之性”,就是要充分发挥自然万物各自的本性,根据这些本性来处置,而不是依据人的主观想象,这样才能“赞天地之化育”。他在《西铭解》中提到“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位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朱熹认为,“赞天地之化育”要“若其性、遂其宜”,就是根据动物和植物的各自本性,给予适宜的对待,然后自然地能使得万物完善,这不是外在的强加。此外,朱熹还指出,这种活动“皆是事实,非私信之仿像也”。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圣人“赞助”与“辅佐”自然并不是从人出发的,而是要从万物的本性出发。
那么对待自然万物是具体应当怎么做呢?先秦儒家关于生态方面大多强调“时禁”,不是完全禁止人们狩猎或伐树这类行为,而是人们有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如《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要按照一定的时节、万物的节律来安排这些活动;《荀子·王制》篇提到的“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朱熹继承例了这些观点,《朱子全书》中有提到“圣贤出来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如草木昆虫,未尝不顺其性,如取之以时,用之以节:当春生时‘不殀夭,不覆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所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惟是先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圣贤要通过顺应万物的本性来开发自然,比如春天的时候不能砍伐树木等,因时节来开采,这样才能使得万物各得其所,而前提则是要先认识到自然万物的本性,而不是一味盲目地索取。
人通过“尽物之性”,充分顺应万物的本性,并且“取之以时,用之以节”,不随意戕害自然的动物和植物,这是朱熹关于开发和利用的具体要求和途径。他认为,这样做最终能达到人“与天地参”的目标,“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是儒家提出的一种至高至极的人生境界,强调的是人和自然之间分职而又协调达到相统一的理想状态,意为与天地功德并立而为三,这是一种人与天地和谐的状态。
总的来说,朱熹通过论述人与物的本性出自同一本源——天,说明人与万物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各自的气禀不同,导致人与物之间的差异,而天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因此需要人来“赞天地之化育”,人在这个过程中要顺应万物本性,“取之以时,用之以节”,最后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朱熹这种生态观是从自然中万物的本性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其最终目的与核心是人与万物的和谐。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相比西方的生态保护观点有其独特之处,既不同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也不同于“非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活动视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作恶之源的观点,如彼得·辛格《动物解放》强调解放所有的动物。朱熹既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中心,同时又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作为促进并达成这种和谐的主导力量。这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独特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的智慧。
《动物解放》,彼得·辛格/著,青岛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