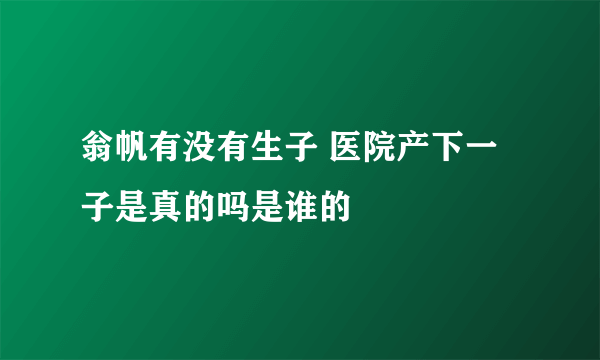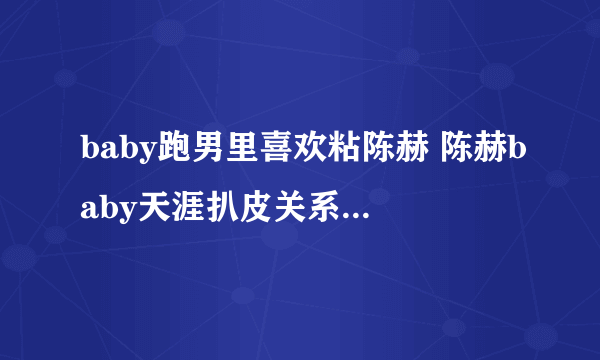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记忆中的秦淮花灯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大南京来斯#
记忆中的花灯 文/方益松
一到正月,满街花花绿绿,皑皑白雪映衬,一片灯的海洋。
正月十五闹花灯。极喜欢这个“闹”字。是冰天雪地里,凌寒的腊梅兀自开放,俏枝迎春,花开有声。凡俗的日子,有了希望,满心的欢喜与企盼呢。
花灯,又名“彩灯”,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品。起于汉,盛于唐。而今,早已由最初的照明功能,逐步演化为兼具生活功能与艺术特色。通常以竹木、绫绢、丝穗、彩纸等材料,经彩纸裱糊,编结刺绣而成。比较考究的,还可配以剪纸、书画、诗词等装饰制作。
“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这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的描述,明朝画家唐寅亦有诗云:“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心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到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寥寥数语,将花灯的华彩与乐趣,毕现无遗。
大约20年前吧,每年寒假,我都坐了车,迢迢的,从父亲插队的沭阳赶回南京。原因有二,一是代替父亲,看望年迈的爷爷;二是帮爷爷扎花灯。此两条,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一颗小小的心里,亦有着对都市的向往。拥挤的弄堂、花花绿绿的糖果。这一切,时时在诱惑着我。记忆中的花灯,最为鼎盛的,当数秦淮河文德桥沿岸。雾霭将现,华灯初上,便有游人如织,人声鼎沸。无数灯盏,琳琅满目,形态各异。或挂或提或拉,灿烂了河水,也点亮了心情。
儿时的记忆里,吃的,无非是稀饭咸菜,穿的,也只有或灰或蓝的粗布衣裳,日子过得紧巴着呢。所以,年前扎花灯,于爷爷来说,就是一种殷切的企盼。卯足了劲,眼巴巴的,像农民守望着地里的庄稼。一年的日子,都指着它呢。爷爷戴着老花眼镜,用那双布满青筋的双手,操竹刀劈开竹子,削片,卷成圆形或椭圆形,烘烤,定型,再用细铁丝缠绕,固定,做好花灯的骨架,裱糊上彩纸。一张普通的皱纹纸,经爷爷一双巧手,或剪或折,顷刻,就成了一朵出水的芙蓉。我在一旁,红肿着小手,帮不上忙,也就是剪个兔子眼睛,刷点浆糊,或上轮子。那时的花灯,轮子是水泥铸的,厚实稳重,可以保证花灯在拉动时不易倾倒。
元宵节前后,满眼满眼都是灯的海洋。我和爷爷用长长的竹竿,嘎吱嘎吱,抬着一串串花灯,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一挂好。爷爷疼我,总是买来冒着热气的莲湖糕团,呵呵笑着,看着我吃完。自己则背过身,偷偷啃那又冷又硬的窝窝头。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每天晚上,爷爷总是咳咳喘喘,对着昏黄的灯光,数那一毛两毛的钱币。那种目光混浊而深远,似乎穿透岁月的艰辛,于苦难中盼出一丝甘甜来。看着驼着背,双手被竹刺、铁丝扎得血迹斑斑的的爷爷,我常问:“爷爷,您为什么每年都要扎花灯啊?” 爷爷不语,只是微笑着,用那粗糙的松树皮般的手指,轻轻刮过我的鼻子。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无言的慨叹啊。
时光毕竟犹如流水,爷爷已作古多年,家里的日子,也终于日渐红火了,父亲也不用再去传承爷爷的衣钵。这几年,街头逐渐出现了一种机器制作的塑料花灯,造型别致,颜色鲜艳,但却总是过分完美,没有了手工制作的粗糙与质朴,失却了过年的韵味。如今扎花灯的艺人,早已不再以此为生。只是,把扎花灯作为美好日子的,一种修饰与点缀。更有着,对过去那段艰苦日子的深切怀念。